從閾間神學看舊約《以斯帖記》──信仰在曖昧與邊界中的再發現(作者:蔡錦圖)
[上圖是猶太會堂在普珥節頌讀的《以斯帖記》手抄本。]
(下文是我在某本書稿的部分撮寫,有許多讓我深思之處。鑑於我寫的書沒有多少人看,尤其是涉及複雜的概念,但那些思考一直纏在我的腦中,倒不如先拋磚引玉,略作分享。冗長沉悶之處,敬請見諒。而且,這段落會否最終出現在我的書中,尚是未知之數。)
一、當上帝「不在場」的神學省思
《以斯帖記》在整本聖經中,是一卷既熟悉又令人不安的書卷。它講述一位被擄的猶太女子以斯帖,在波斯帝國宮廷權力結構中,被擢升為王后,最終拯救民族免於滅亡的故事。在以色列歷史上,只有三次如此接近滅族的危機:出埃及之時、以斯帖之日,以及納粹德國治下。現今猶太人的節期,主要是與這三次危機得蒙解救有關。
然而,這卷書最引人注目的地方,並不是戲劇性的情節,而是——上帝的名字一次也沒有出現。這種「神隱」現象,使《以斯帖記》成為信仰的邊界文本:一方面,它敘述猶太民族的存亡;另一方面,它呈現了一種沒有明顯神蹟、沒有直接啟示、沒有先知聲音的信仰實境。
對許多現代信徒而言,這樣的處境反而更加貼近生活:我們也常身處上帝似乎沉默、現實充滿模糊與矛盾的時刻。在上帝的沉默中聆聽,可作為《以斯帖記》的詮釋起點。
文化人類學家阿諾爾德·范亨內普(Arnold van Gennep)與維克多·特納(Victor Turner)在二十世紀提出的「閾間」(liminality)概念,按此發展的「閾間神學」(Liminal Theology),或許最能詮釋二十世紀甚至二十一世妃的時代狀況,而且能讓我們更深地理解《以斯帖記》所描繪的信仰經驗:那是一種「介於秩序與混亂之間」的狀態,一種「尚未確定、卻孕育轉化」的神學空間。
二、閾間神學的視野:信仰在「過渡」中的形塑
1. 「閾間」(Liminality)的意涵
「閾」( limen)原意是「門檻」,在文化人類學中,指的是一種「過渡的中間狀態」。范亨內普在研究傳統社會的「通過儀禮」(rites of passage)時指出,人生重要轉變往往經歷三個階段:分離(separation)、閾間(limen)、重聚(incorporation)。在「閾間」階段,舊的身份已被解除,但新的身份尚未建立,人因此處於「介乎之間」的狀態。
特納進一步強調,「閾間」不只是過渡,更是一種創造性的混亂。在這期間,社會結構被暫時懸置,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重新被定義,新的意義有可能誕生。
這個概念引伸用於神學上,尤其是在充滿戰亂和流離的二十世紀,尤其適合。「閾間神學」(Liminal Theology)是一種在「門檻之間」思考信仰與經驗的神學,關注人與上帝、聖與俗、秩序與混沌、已知與未知之交界狀態。閾間神學指出:信仰往往不在穩定的秩序中被塑造,而是在不確定、破裂與邊界中被重構。上帝常在「門檻」之處顯明祂的作為——不是以支配者的姿態,而是以隱藏、等待、反轉的方式。
2. 以斯帖記作為「閾間文本」
按此取向,《以斯帖記》正是一卷典型的閾間文本。它發生在猶太人被擄的歷史之後,地理上遠離聖殿與應許之地,神學上遠離祭祀、律法與先知的中心。整個故事發生在「外邦帝國」的宮廷之中,猶太人身份被邊緣化、信仰的象徵被隱藏。
最近英國盛傳工黨會制定減少移民的政策,雖然一直有零星的說法謂不會影響BNO visa,但在大風向之中,誰能保證任何事情。我輩香港人從來是浮萍飄泊,九七前後沒有分別,都是天涯游子,憑著智慧和努力,勉強生存下去。然而,何處是落葉歸根之所,大概沒有誰可確定。
以斯帖自己正活在「閾間」:她既是猶太人,又被迫成為波斯王后(我在《以斯帖記》的註釋中,有足夠理由證明她被選入宮是迫於無奈);她的民族身份必須隱藏,直至危機爆發;她介於順服與抗命、恐懼與勇敢、沉默與宣告之間。這種「身份的懸置」,正是閾間經驗的典型表現。
《以斯帖記》整個敘事也呈現一種神學的閾間性:上帝不直接行神蹟,卻在人類的偶然與政治的權謀中運作。命運的反轉——從末底改被要吊死到哈曼自己上了刑架——正顯出「隱藏的天意」(hidden providence)。這種「在沉默中的作為」正是閾間神學的特徵:上帝在邊界中臨在,在缺席中顯現。
三、信仰轉化的三個階段
1. 分離:被迫進入他者的世界
《以斯帖記》的故事伊始,以斯帖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庭與民族,被帶入帝王後宮。這是她「分離」的階段:與原有身份、信仰群體分割,進入一個陌生且支配性的體系。她不再有主體地位,甚至連名字也從希伯來名「哈大沙」變為波斯名「以斯帖」(意為星辰,亦可能暗示「隱藏」)。
在整部舊約中,只有《以斯帖記》不以猶太名字,而是以外邦名字稱呼主角。這種隱藏身份,閉口封聲,絕不是自行的選擇,而是現實的無奈(我現今寫的任何文章和書籍,也要如此小心翼翼,或許可以明白一點以斯帖和末底改的心情)。
在這種狀態中,信仰似乎被壓縮成沉默。以斯帖在書中從未曾公開祈禱(這也是舊約中唯一如此的主角),也未表達宗教抗爭;但這種沉默並非不信,而是一種「在被迫的邊緣中保持可能性」的信仰姿態。
閾間神學指出:信仰有時不是大聲宣告,而是忍受模糊的過渡期。在文化與政權夾縫中的信徒,也常處於「信仰的閾間」——既要忠於信仰,又要在體制中尋找生存空間。以斯帖的沉默不是妥協,而是一種策略性的信實。
2. 閾間:面對危機的再定義
當哈曼的陰謀揭露後,以斯帖進入故事的轉折——也是她信仰的「閾間期」。她必須決定是否冒死晉見王,揭示自己的身份。末底改的勸勉是整卷書的神學核心:「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?」(斯4章14節)
這句話本身就是一種閾間語言:它沒有明確的神諭,只是「焉知」(who knows?)。在上帝沉默之中,人只能以不確定的信心行動。以斯帖回應:「我若死就死吧!」(斯4章16節)這句話標誌著她跨越了門檻——從被動的角色轉變為主動的行動者,從「被他者定義」變為「在信仰中自我確立」。
閾間的力量在於,人在失去確定性之時,反而更能經歷信仰的真實。我在二十多年前被確診有先天性心臟病,在死亡邊緣上徘徊,習慣了把每一天視為最後一天。然而,這二十年來卻是人生最豐盛的日子,做了比前半生多許多的事,或許正是由於不知有沒有明天,就把今天視為最重要的一刻(故此,若我在facebook有一段時間沒出現,不用擔心,我或許去了旅行,或許去了天國而已)。
以斯帖的決定,不依靠外在神蹟,而依靠在「不確定的神」中確信祂仍在。這是一種信仰的成熟,也是閾間神學最深的洞見:信仰的確定性,不在於掌握上帝的計畫,而在於在不確定中仍選擇順服。
3. 重聚:反轉與更新的神學
當《以斯帖記》故事進入高潮,上帝的「隱藏作為」終於顯露。哈曼被吊死、猶太人反敗為勝、普珥節(Purim)被設立以紀念拯救。這是「重聚」階段:新的秩序誕生,民族身份重新被確認。
然而,這個「重聚」並非回到原點(更不是猶太人回到本土),而是帶著閾間的記憶。普珥節的設立象徵一種「邊界中的喜樂」:在外邦帝國中,猶太人仍能慶祝上帝的救贖;在看似世俗的世界裡,信仰仍能找到禮讚的空間。這不是聖殿的敬拜,而是流亡者的敬拜——沒有祭壇,卻有見證;沒有顯現的神,卻有存留的信心。
從此,猶太人不再是固守在自己土地的民族。當然,他們並不是完全理解的。到了新約時代,耶穌告訴他那群猶太門徒,要從耶路撒冷去普天下,讓他們擁有一個從《以斯帖記》已建立的視覺:他們無須固守在一片土地上,而是以普世為心志。
這種「閾間的重聚」,正是信仰生活的寫照。我們活在未完成的國度中——基督已來,卻仍未完全;救恩已啟動,卻仍等待成全。我們正如以斯帖般,活在「已然/未然」之間的門檻上,見證上帝在沉默與曖昧中的恩典。
以斯帖的故事提醒我們:
當上帝沉默,信仰仍可活;
當身份模糊,忠誠仍可被見證;
當歷史混亂,恩典仍在運作。
舊約的詮釋在文學層面常被視為政治寓言或民族記憶,但在神學層面,這卷書更是對「信仰邊界」的深刻探索。它邀請我們進入那「不確定卻真實」的空間——在門檻上遇見那位一直同在的神。我們的信仰常在文化、身份與時代的邊界上被考驗:在傳統與現代之間、在信仰與制度之間、在語言與文化的轉換中。然而,正如以斯帖一樣,這些邊界不是信仰的障礙,而是恩典的場域,那麼如今身在外地的異鄉人也是如此。
(原文及圖片來自作者的臉書帖文,承蒙允准轉載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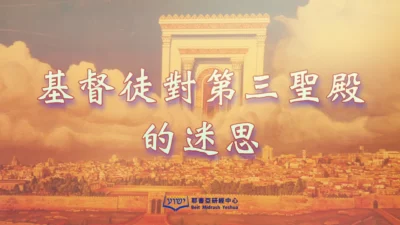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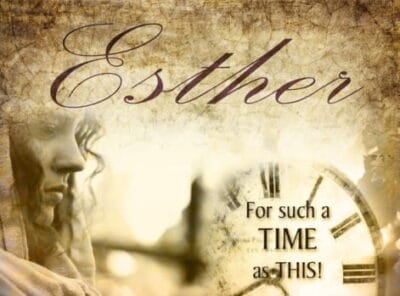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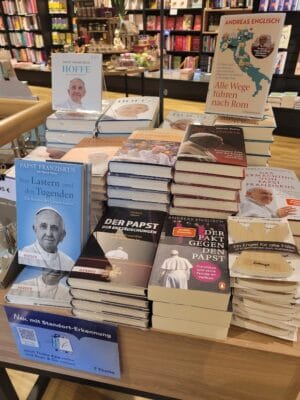

-400x261.jpg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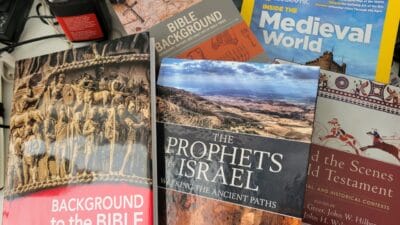
Herbert-Chan-400x260.jpg)
-400x260.jpg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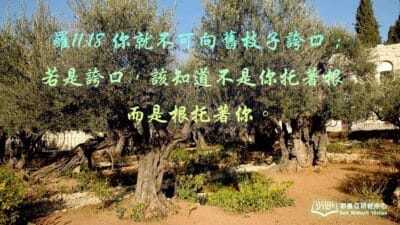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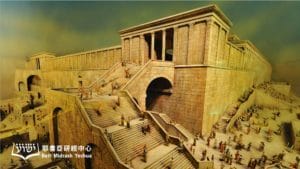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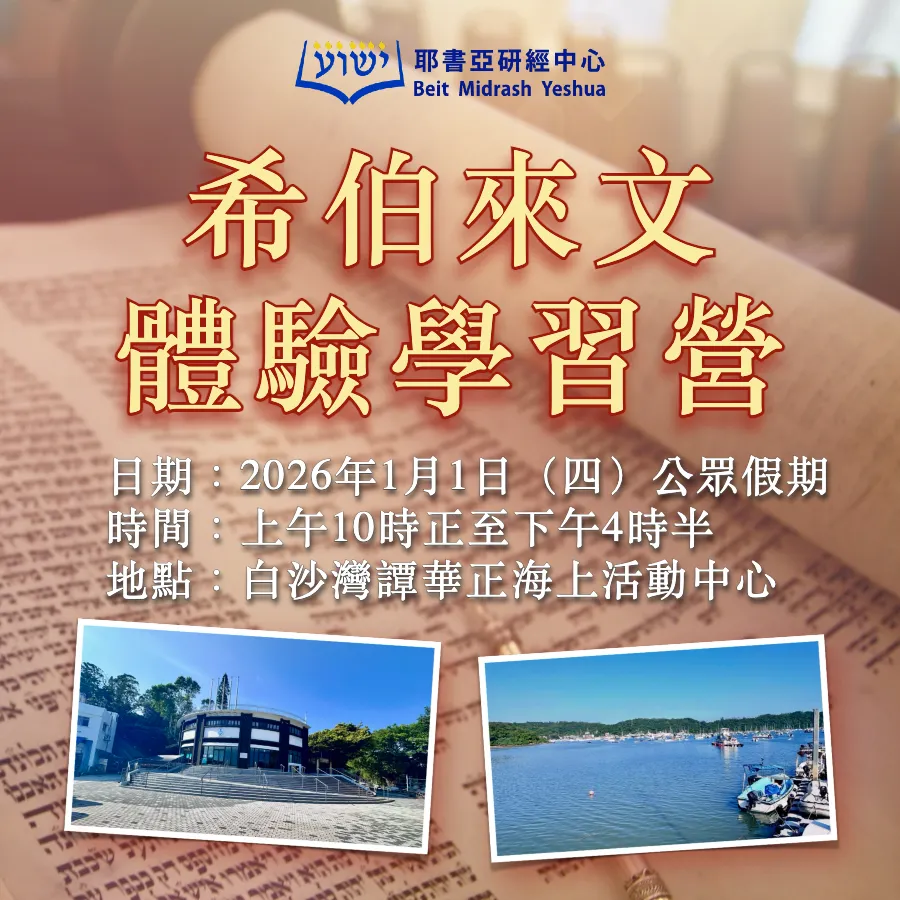
關於作者